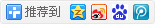待周蕓蕓從午后小憩醒來,孟秀才早已從街面上回來了,他本人在由廂房改建的書房里寫著字。周蕓蕓過去時,他指了指擱在書房小圓桌上的包裹道:“我把銀子都擱那兒了,你先收著。回頭用得差不多了,記得要提前支會我一聲,我好再去尋張兄。”乍一聽這話,就好像張掌柜是他的錢莊似的。周蕓蕓好笑之余是滿滿的感動,一個男人愿意將全部身家都交付出來,從某種意義上來說,哪怕不是愛,至少也有敬重。
>玄幻奇幻 > 第一寵姬最新章節(jié)目錄

推薦閱讀:
十媽生一胎
,
一胎倆寶,老婆大人別想逃,
裝不在意,
生活不易,朱雀賣藝,
身體秘密 感官世界
,
夏碎·起床氣,
當不上帝皇俠的我在美漫當司機,
人形充電寶,
嬌小初叫VIDEOS摘花第一次
,
美漫之阿斯加德的戰(zhàn)神
- 1、橫行霸道
- 2、吃瓜吃我到自己(第四更)
- 3、攻占盛京撫近門
- 4、章三下:太液池兒女牽衣,銀臺門一夫發(fā)難
- 5、不懂他的操作
- 6、被退婚的太子妃(7)
- 7、境界差別,深不可測
- 8、鳳靈韻催眠鳳無雙(催更滿288加更)
- 9、第一節(jié) 端倪(一)(修正)
- 10、連哄帶騙,曾經(jīng)的歐洲最佳中場!
- 11、番外章 惡鬼
- 12、第一次吻
- 13、西城龍爺
- 14、你的愿望
- 15、什么狗屁火勺
- 16、無上
- 17、:后續(xù)
- 18、未來的計劃
- 19、老好人三號
- 20、吃飽了撐的
- 21、初見焉未央
- 22、親自核實
- 23、木頭彈頭
- 24、都市怪談
- 25、浪漫的想法和現(xiàn)實的殘酷
- 26、前路被堵
- 27、神廟
- 28、我要去香江!
- 29、三角進攻
- 30、自己的女人都管不住,活該被綠
- 31、刺激情敵的辦法
- 32、:打臉陸德明
- 33、嫂子心虛
- 34、月下歌謠
- 35、我單純的妹妹
- 36、我家夫人面皮薄,她要害羞了
- 37、神光寶鏡
- 38、安師兄筑基
- 39、矯揉造作
- 40、面圣
- 41、答應他
- 42、前未婚夫來了
- 43、歸途遇襲
- 44、錦龍商會
- 45、至尊術(shù),人皇劍訣
- 46、降服鬼娃劉二娃
- 47、攝政王的庶女王妃(三十一)
- 48、88 山體滑坡
- 49、那手環(huán)本來是我的
- 50、破繭重生
- 51、狂人登場
- 52、壞了事兒
- 53、微型炸彈
- 54、庭前斗武(求收藏,求追讀)
- 55、她必須得參與
- 56、獨屬的經(jīng)歷(第三更)
- 57、好!很好!非常好
- 58、你得加錢
- 59、太愛裝逼了
- 60、步法
- 61、靈狼血脈
- 62、老男人的無奈
- 63、黑云壓城城欲摧
- 64、兩顆(一更)
- 65、小珩又被坑慘啦~
- 66、:她們該不會是一個人吧?
- 67、陳林的新任務
- 68、富家小姐愛上窮小子
- 69、金玉其外
- 70、夏洛克·宋
- 71、謀算,初見
- 72、一刀流?(上)
- 73、強啊
- 74、夜大
- 75、銘文銘紋
- 76、32,清算
- 77、:少女開局
- 78、知錯能改,善莫大焉
- 79、滑倒了
- 80、抵臨
- 81、豐盛一餐
- 82、暑假,搞事情(一)
- 83、感動(召喚推薦票)
- 84、:有種你過來殺我啊
- 85、南風入宮
- 86、:頂級傷害計算
- 87、瘋狂的逆襲
- 88、被白眼狼妹夫吸血的大舅哥9 戳破塑料……
- 89、隕落 (29)
- 90、94楊登歡的疑團
- 91、不再計較
- 92、太歲日
- 93、玉綾雷斬
- 94、吾有龍膽亮銀槍
- 95、你老娘我搞得定
- 96、011 榜眼狀元單挑
- 97、勿謂言之不預
- 98、祖龍御用?國博館被炸出來了!